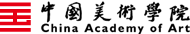21世纪经济报道 《21世纪》:我们注意到,这次展览的布局很有特点,每一个展厅的名字都是并置的,如“重屏-东方葵”、“层览-葵平线”,这样的布展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?
许江:这次展览有两条主线,一条是葵的主线,就是“东方葵”、“葵平线”和“一花万果”。“东方葵”跟我十年前、八年前画的葵已经很不一样,这里的葵被连根拔起,编结到一巨大的构架上,在构架上它们重新生长,蔓生叠压交错生长,形成一种整体的趋势,像一个社会;在葵平线里,一个个四季的葵园,像中国画长轴一样横陈在面前,在这里再现中国古代山水横轴俯瞰的传统,我们俯瞰这些葵园,一层山水、一片葵园,我们在葵园当中行走,好像穿梭在一个葵园的四季中一样;第三部分是铜雕的葵,不是葵盘胜似葵盘的表达方式和四周墙上群画的水彩的葵园,形成了一种葵的特有的感觉。
另外一条主线,是关于“观看”的,“重屏”“层览”“综观”。“重屏”就是一座屏风一座葵山,九重屏风九道横山,群峦叠嶂,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一个扑面而来的“东方葵”的表情,在这个东方葵的表情后面可以看到一代人的精神图象;到了层览,大尺度的观看叫“览”,这里带出一种新的观看的方式——这种新的观看方式又源于中国式的观看方式,中国人看事物历来就不是站在山对面看山,他会在山上游览,最后群山在他心中留下印象,现在我们在葵园当中穿梭,代替这种观看;第三部分是“近抚远观”,一定带来一种别样的“浅深聚散,万取一收”趣味……
这两条主线其实都在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问题。葵的主线面对的是我们主体问题;“观看”的问题面对的是图象时代,我们如何真正了解图像的本质,使我们的观看变得深沉,不会因为工具的简便而使我们的观看变得浅薄。
《21世纪》:您是试图通过“观看”方式的“发现”,让人们去思考“图像”的本质吗?
许江:其实在图像时代,绘画在写实和表达事件方面已经根本比不上现在的图像工具。数字图像技术已经不再需要古典的再现中不断地、缓慢地组织着的触觉内涵。它用一种象征编码取代了肉身之感。在这里只有一种质量,玻璃的质量。在这里,手被减缩为手指,一个按在视觉键盘上的手指头,一个内在的、视觉开关上的手指头。
但是,当我们重新回到“观看”的时候,我们会发现绘画的重要性。绘画是一个漫长的塑造的过程,是人与世界同在的过程。还原到我自己的绘画中,葵不仅是我旷日持久的绘画对象,而且是我们自己生长的一个新的生命,我们在里头生产,葵就是我们的一切,葵就是我们的大地,葵的欢乐是我的欢乐,葵的痛苦是我的痛苦。还有绘画如何运用笔和色彩,带出我们生命的特点,东方人的特点,怎么把我们自己的个性打开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。
“体象”
《21世纪》:刚才您提到,绘画过程中,如何运用笔和色彩,带出我们生命的特点,东方人的特点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。以前,您也多次提到如何在油画中表达东方的情感等类似问题。
许江:油画是舶来品,油画的背后是一部厚重的西方文化史,它本身是一种西方语言。这样一种西方语言到中国来已经落地生根,那么它的色彩,它的力度,它的品位,如何变成中国人的东西(语言),当然不是为了变而变,如何传递中国人的情感,完成创造性是转换,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。
《21世纪》:刚才在给我们介绍画作时,您曾经提到,这十年,主要是在“格”葵,能不能做进一步的阐释?
许江:十年来,我不断地去研究葵,去穷极它,最后发现的“体象”,既不是我,也不是葵,而是葵和我都包容在内的创造者。“体”很重要,这个体必须是本人的植入,体就是本人,本人的植入,才能有所体察。而“象”是东方人一种非常重要的想象性的中介,是我们和事物亲近、理解事物的内在和整体的最重要的中介。“象”不是独立于对象与主体之外的第三者,而是包蕴了主体与对象在其中的此时此在的生命形式。通过直观,来调动身体独见的感受力,来面向“象”的生命形式,这是中国绘画创作和感人的秘密,也是中国视觉文化精神的诗性内涵。
“向西归东”:老葵们的历史使命
《21世纪》:您的葵,被当作“向阳花开”一代人的精神史诗。问题是,在经历社会转型和如此大的变迁后,“向阳花开”的一代人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认同吗?
许江:清代书画名家恽南田说,群必求同,一个群体必然有相同的地方;求同必相叫,有同的地方要叫出来的;相叫必荒天古木,什么叫荒天古木?我觉得我的葵就是荒天古木,我理解的荒天古木就是有历史记忆的地方。
前不久,孙歌到我的画室。初次见葵,几乎是在瞬间,孙歌即表达出她的共鸣。后来她在文章中写道:“我感到了莫名的震撼。这劫后余生的精灵,这成片成片不起眼的葵所构成的平凡而伟大的超越,唤起了我心灵深处的生命感觉,复苏了某些早已沉睡的情感记忆。曾经有一段历史,属于葵。那是包括许江在内的我们这代人共享的历史。”
她还写道,“老葵们经历了分化,一如许江笔下葵墙的杂乱与纠结;然而,分化了的葵仍然是葵,历史总是给一代人留下让他们可以彼此辨认的印记。”
我画的葵,表现的是一代人的激情和命运的长歌。我们这代人都在里面看到自己,每次看到葵,我们心里就想起我们的青春,我们的心中就歌声荡漾,我们某种生命的记忆就会被瞬间点燃,然后我们的一代人的生命记忆、一代人的成长经历,一代人的饱经打磨的价值观通过葵呈现出来,所以我说葵的激情、热烈、燃烧、向阳、奉献、沉重的表情是这代人的表情。
在“狂飙的葵”面前你会听到一种呼喊从中发出来,它揭示了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命运、历史性,葵园的使命就是揭示这代人的历史性,不是历史,而是历史性,我们这代人独特的历史性。它是什么?我个人觉得这个历史命运、历史性就是“重归东方”,这个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命运,重归东方,因为我们的教育就告诉我们东方日出,我们永远都相信,所以我们为东方骄傲,这个是埋藏在我们心里非常强烈的,所以我们知道“东方既白”,东方很快就会亮起来了。我们曾向西方学习,学习的目的是为东方带回来什么,如何来建设东方,所以我们走的是一条“向西归东”的道路。
《21世纪》:“向西归东”是非常形象且深刻的一种表达。我们知道,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艺术家都是一心“向西”的,但最近几年“发现传统”或“重返东方”有成了一种潮流,对此,您怎么看?
许江:我觉得不要简单的去理解“东西问题”,东方葵的东方,不是西方臆断中的东方,比如说东方是线性的,西方是面的,东方是感性的,西方是理性的,东方是重线条的,西方是重色彩的等等,那种东方的臆断,一方面停留在对中国古代诗词、琴棋书画、梅兰竹菊的想象当中,另一方面仍然对当代中国面向世界进行的一个时代的奋斗视而不见,我觉得我们讲的东方是中国当代火热的沃土上那个不断发展的东方,是真的活的东方。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会偏向这边,可能有时候会偏向那边,可能有时候会特别的沉重,可能有时候会特别的纠结,没有关系,但是内在总是有一种坚强,总是坚信日出东方,这点我觉得是这代人的非常特殊的。
我们这代人相信,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,但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中就得救了。我们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。当然,我们不能丢掉传统,如何让传统最优秀的东西活在今天,这恰恰是我们思考的问题。
现在,我们已经没法简单地谈论东方和西方了,东方已经不纯粹,我们已经把很多西方的东西成功消地化在东方了,比如说现在衣食住行还有哪些是纯然的东方?我们茶米为食这个我们继承下来了,但是现在的孩子三岁就吃麦当劳。这个方式的巨大变迁使得我们在思考东方和西方这个问题的时候,一定要警惕,既不能过于强调所谓的东方,把传统的东西一成不变的拿下来,觉得今天只要把传统带回来就解决一切问题,这不可能;但是也千万不能够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全球化的潮流走,还是要把东方那些最深刻的东西理解好,这是艺术教育最重要的工具,这是艺术教育能够为未来的中国、未来的世界提供奉献的地方。(编辑 李二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