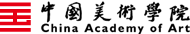|
文/李如艳
江西广昌,有名的莲乡,月色浸染荷塘,大朵大朵的白色荷花,在清冽月光的晕染中,出淤泥而不染,遗世而独立。张伟民拿着写生本,竟有些看呆了。1300多年前李白说: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李白与酒作伴,共享月光,此刻,张伟民与花同月,共沐清辉,虽有淡淡寂寥,又何尝不是人生之幸? 手中的写生本几十年来不知换过了几百本,花开花落,人生一甲子已过,与花俱老。
与花相伴
张伟民是1955年生人,数数光阴,一甲子已过。浸淫在花鸟画中几十年,老友喊他上北京画院办个展,张伟民首先想到的就是“与花同月”。
“在花面前,我是个知足的人。”张伟民这样说,几十年写花画花,花已经成为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存在,是知己,是爱恋,是理想的彼岸。
张伟民是一名典型的杭州人,自小就生活在钱塘的湖山之间,西湖就是他家的“后花园”。西子山水的滋养,给张伟民的丹青生涯绘制了最初的温润底色。
从小张伟民就爱画花鸟,后来在中国美院研究生阶段,他跟随陆抑非学习,全才导师给他奠定了视野和学术基础,创作开始全面铺开。
他不满足简单的花好月圆,一花一草也要传递出个性的精神神态,融工笔的勾勒、渲染与没骨、兼工带写、泼墨法为一体,悉心勾勒着万物的微末变化。区别于传统绘画的色彩原则,他以情为轴心,大胆尝试对比色和丰富色彩的调动,却能处理得毫不流俗,具有现代意识流的美学特征。
有一次,张伟民到香港去办个展,有人问他,你从扎实的传统学习中走过来,创作却为何如此现代?
张伟民笑笑,引用了戴望舒的一句诗:“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,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记你。”他进一步解释,“把它运用到绘画上,其实是说传统与创新的关系,我们在传统中得到良好的营养,但现实的冲击和表达的欲望更重要。”
在他看来,工笔画经历过两宋的巅峰时期,经过明清后却落入刻、板、僵的窠臼。“当我以元明清文化发展的审美思想回头审视宋画,发现宋画在个人心性表达上还有诸多发展空间。而艺术的落脚点恰恰在于发现自我,表达自己,检验人类的基本情感。”
除却绘画的时光,张伟民也是那个年代标准的文艺青年,喜欢写作,散文、现代诗一应俱全。他的画册画作与文字总是相辅相成,那些诗一般的文字,凝结了他日复一日对艺术的思考,对生活的感悟,而这所有又最终反哺于画面,呈现出独属他的面貌。
景语皆情话
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中云:“一切景语皆情话。”所谓“景语”成“情语”,“情景交融”说的大抵就是这样吧。
置身自然中,张伟民是敏感的。“听花开的声音”,他似乎摒起呼吸,张开所有的感官,去拥抱一花一草。在《风月无边》、《万木霜天》、《春之潜流》、《乱红飞过秋千去》、《清质澄晖》等诸多作品中,你似乎可以看到花开的声音,听到霜叶的律动,触摸到心灵的跳动,感受到了生命的灌溉。
他把这些自然景致营造进朦胧的、虚幻的、静谧的氛围中。他说:“创作尚使我的画怀着青春的梦想。”画面中呈现的张伟民永远是个年轻人,有着诗人般的忧郁与感伤。
其实在创作中,他很少对物象进行直接的、简单的描绘,而是把分散的、无数次的美的感受与认识,逐渐集中起来,明晰起来,舍去了那些与主题无关的细节,最终把生活中的实景转化为画面中朦胧静谧的画境。所以我们看他的画,总是既“熟悉”又“陌生”,既具体又超越自然。这些经过画者重建的现实,渗透着画者的精神情感和审美认识,是心境与意绪的袒露。
这次展览中,张伟民有一张大画叫做《一池千古月》,是2016年的新作。然而说起此画的由头,却要追溯到30年前的苏州拙政园,里头有一个十八曼陀罗花馆,是以前一户有钱人家姨太太居住的地方。然而花馆已是人去楼空,只余这馆前的池塘与月色依旧。张伟民很感叹,人生就是如此短暂而匆匆。许多年间,此情此景,挥之不去。今日终于下笔绘就了这张《一池千古月》,用了紫藤的画法,却只用最简单的黑白两色来勾勒,他说“长藤不驻岁月”。
然而画完之后,张伟民觉得人生若只是如此,也太悲哀了。于是他又画了第二张画——《小径四时花》。池塘边小径上的花开花又落,一群鸟自由自在栖息在此,不随人事而变迁。画中,他创造性地将白玉兰点染成嫩绿色。
这绿色即是张伟民心中的色彩。人人说工笔画是对现实的摹写,张伟民偏偏要打破这种程式化的认知。他说,色彩的运用既是画面的需要,又是画家情感的外化,传达的应该是画家心灵深处的审美感受。“谢赫六法中说‘随类赋彩’,但我遵循的是‘感情色彩’。”
3与花俱老
得知张伟民北京个展的消息,好友毛建波脱口而出了此次展览的题目“诗性工笔”。毛建波说,诗性是画家面对自然事物情动于中、胸中郁积情感的勃发。胸中有诗意不难,难的是在画面中呈现诗意。
多年来,张伟民坚持不懈的写生观察,唯美梦幻的意境谋划,实入虚出的绘画语言,工笔意写的“营造法式”,大块的墨色渲染,挺健的细笔勾勒,共同形成其作品的性情。
在北京见到张伟民时,他正在忙碌的布展中。两层的展厅,近百件花鸟作品,既有宏幅巨制又有团扇小品,于10月19日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。布展现场的张伟民语速急促,指挥有力,对于展陈想法明确,毫不犹豫,常常三步并两步叫年轻人都跟不上。这个时候的张伟民,似乎与躲在画作背后感春怀秋的诗人不太一样呢。
“我所有的浪漫,都给了花,都融进了画里。”张伟民笑言。多年来,张伟民总是不可避免要承担一些社会职务,“我巴不得分分钟就做完工作,好多留一些时间投入创作中。”他有时也常常会在日记里发发牢骚,或者跟也有志画画的女儿靓亮谈谈心。他是真的热爱画画,他常说“绘画需情不自禁,不要身不由己地创作。”他苦的是情不自禁时,却常常身不由己没时间画下来。
你看他的白描写生稿中都非一蹴而就,相反会大面积留白,日后他会将这些白描稿反复打开,来回审视平衡调整,记忆碎片在慢节奏的重复中拆解组合,等待情境的到来最终合而为一落于纸上。
如今,他还会为了补画作的一片隔水浮萍去曲院风荷写生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他戴了一辈子的近视眼镜,逐渐被老花眼镜所代替。而曲院依旧美丽,平湖秋月照样明媚,花港的牡丹仍然像游园的稚童那样生机勃发。数几十年的写生、创作,创作、写生,年华的流逝与轮回,都被张伟民融进“诗性工笔”当中。
他把自己这个年龄叫作“花已向晚”,“但60岁并不是消极的,不是悲哀的,它是更倔强的,更体现人类终极思想。”
与花相伴,与花俱老,随花逍遥,真也不失是一种幸福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