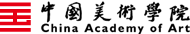许江与葵
一场十五年的邂逅

许江 扫雪 50×300cm 布面油画 2016年

许江 孤陔 200×156cm 布面油画 2018年5月
本报记者 陈洁 江凌
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间,如果来到上海民生美术馆,便能邂逅艺术家许江构建的葵园世界。
“葵颂——许江近作展”不久前在这里落下帷幕。既担任着中国文联副主席,又作为中国美术学院一院之长的许江,在面对自己的艺术作品时,真诚不减,激情仍在,但在神色和手势中,多了一丝柔和:“葵不仅仅是我的记忆。我的每一天,我的真实感受都在这里面呈现出来。它是活的。”
行政工作这么忙,怎么还有精力创作呢?在展览现场,有人这样问。许江哈哈一笑:“被‘逼’的呀!美院里大家都在画,我不画怎么行!”正是这一“逼”,“逼”出了“废笔三千”,也“逼”出了这一次的大型近作展。
一代人的精神肖像
沿着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独特的空间结构,从上而下,循环往复,许江用富有景深的回溯型展览路线,构建了五个诗化的展示空间:“怀沙”、“野火”、“蔓生”、“铸炼”、“葵颂”。展陈的作品里,除了50余幅油画外,还有系列水彩作品百余幅,以及一系列雕塑与大型装置作品。
无论是层峦叠嶂的巨幅油画,还是铺陈延绵的横卷预览,亦或是悬卧逐浪的如山葵林,场内与场外,野火与华葵,许江将改革开放一代人的坚韧释放在了这些葵里。那无数的葵籽、那火红的葵头,仿佛千山万壑,既有山水的烟云,又像燎原的烈火,这是许江在为逝去的岁月加冕,用永远的燃烧标志一代人永无褪色的激情。
观草木,寄人心。面对草木,东方人总有一种特殊的充盈。在万物和人心的相汇下,草木便有了悲欣和衰荣。“葵”的使命,也在于此。在许江隆重而又浓烈的群葵之下,一代人独特的身世和历史境遇,他们的生命经验与精神气质,通过“葵”这样一个曾经浸泡着青春印记的物种意象得以彰显。
许江生于1955年,1978年进入美术学院。这是“向阳花开”的一代,也是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的一代。他把自己这代人切身的生命经验,转化作历史的表情,凝聚为一代人的精神肖像。许江画葵,是要讲述向阳花开的那一代人的故事。
在中国美术学院90年校庆上,他曾满怀深情地回望过那段岁月:
“红笺向壁影模糊,黄灯呵手争执书。77、78一代人的远忆只若童话,但就是在这样境域中,诗与远方重新在这里聚拢,老美院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精神如秋草薪火,渐渐地跬成星、跬成光、跬成焰,渐渐地回返校园,回返青年的心中。从民间、从底层、从木板沥青的可能的空间里,化作自我觉醒、自我救赎、自我批判的力量。一个新的从未有过的童话般的景色又在校园里悄然铺陈。东楼77级油画班同学与78级研究生辩论,萌发最早的零度绘画的端倪;附中楼的某个教室被清空,大字报铺天盖地,中国最早的波普现象在这里亮相;楼上的空着的教室突然繁忙,几幅巨书正带着淋漓墨色悬在壁上,默默地把书法带入当代实验的田园;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陈列馆的毕业展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信息灯,从这里发起中国前卫关怀的诸多端倪;校外通往湖边道旁的墙上,突然贴满巨大的人型符号,述说真正的艺者所关心的社会创造;万曼先生拉起纤维艺术最早的织线;赵无极先生用大扁笔抹去对抽象艺术的妄念;孙宝国的面庞露出中国波普倾向最早的狞笑……”
这个世代,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生命节奏。对许江来说,葵的集体肖像恰恰体现了这代人的生命史——不止于“世代的心情”,而且是一种“我在其中”的历史,一种生命历程和存在经验共同构造出的历史进程,同时也是从时代现场中锻造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品格。在他的笔下,这代人身上曾经有过的苦难、沧桑和依然怀抱的理想、担当,统统被刻画在其中,“我们这代人渐渐老了,就像这片沧桑的葵园,但仍然坚守,仍然挺立。”
与葵的一次次邂逅
英国艺术史家约翰·伯格曾说:“作画的冲动并非来自观察,亦非出于灵魂(灵魂可能是盲目的),而是缘自某种邂逅。”
许江画葵已经十五载,从2003年小亚细亚高原与“葵”不期而遇,他陆续遭遇了生命中数个震动身心的葵园现场,并从这些发生现场中反复自我开启,提炼出葵园绘画的精神内核。今年10月,他来到内蒙古的戈壁滩上,意外邂逅了15年前曾在土耳其遇见的几乎一样的千亩葵田。夕阳西下,大地苍茫,放眼望去,荒原之上的秋葵彼此挣扎呐喊,衰老而倔强。一时间,这十五载沧桑岁月便如庄生晓梦、望帝春心般掠过许江心头,令人感怀万千。
追葵十五载,如何让自己面对葵园时还能保持新鲜与生气,这种“邂逅”对于许江来说,尤为重要。他习惯于在葵园慢慢地看,慢慢地想,拍些照片,写些感受。“在画架上,我和葵一次次邂逅,希望每天都是新鲜的,每张画都是仅此一次的相会。”这种心怀敬畏的焦虑,使得许江与葵的邂逅成为常态。
在展览现场,有观众评价说:“艺术是很相通的,这些画并不晦涩,给人一种生发的感觉。”可以说,许江的葵重新点燃了“诗言志”的传统,其中蕴含一种情志。此情此志,并非流于隐喻或象征性的表达,而是在画家和葵彼此观照的复杂关系之中得以实现。
在葵园创作早期,许江把葵植入浑茫天地,以“俯瞰”的姿态成就一种历史的“远望”;渐渐地,葵脱离了土地,放弃了原野上的诗意,而被摆置在剧场/祭坛之上,成为被献祭、被仰瞻的“无地花”;近年来,葵的形态愈见丰富,或为游目骋怀、含思外览之“葵平线”,或为守静内观、化身千万的“一花万果”。这次,许江用众多峥嵘昂扬的葵头,刻画出人、民、群、众、我的肖像。
艺术家对同一母题的长期积累与描摹,在艺术史中并不鲜见,但国外的绘画或者艺术,很多都带着批判、叛逆、调侃、颓废、嘲讽的意味和习气。但是在许江的葵里,不难体味到东方人真正的生命感受和价值取向。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。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中国人向死而生,面对终极关怀,始终不颓废、不怯懦。
于是,在这无数的葵盘中,“向阳花开”一代看到了自己对于生命的坚守与激情。而年轻一代,则在这样一个葵的语境当中,获得了观察的新视域,他们找到了和父辈交流对话的渠道。在这里,他们看到了父辈的情怀,看到了父辈当年像野火一样的燃烧的青春。
东方葵颂,其貌葳蕤,其威如岳。这是“向阳花开”一代人的精神写照,也是献给这个伟大时代的激越颂歌。